各位老铁们好,相信很多人对道德之乡指的是哪句话都不是特别的了解,因此呢,今天就来为大家分享下关于道德之乡指的是哪句话以及道德与法治对某句话的理解的问题知识,还望可以帮助大家,解决大家的一些困惑,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本文目录
一、庄子的道德之乡是什么意思
《庄子·山木》篇探讨的是庄子的处世之道。在庄子看来,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处世不易,世事多患,很难找到一条万全之路,无论是材与不材,都是十分危险的,山木不材不能保全,雁不能鸣却被杀。即便处于材与不材之间也不能免于拘束与劳累,更好的办法只能是役使外物而不被外物所役使,浮游于“万物之祖”和“道德之乡”。也就是说,仅仅处于材与不材之间并不够,人生更高的境界是应该超脱于世俗的生活之外,彻底摆脱现实社会的羁绊。这种思想与庄子的“道”论是密切相关的,庄子认为人的生活应如野鹿,与自然融为一体,不要做违背自然规律的事,就会达到“至德之世”或“无为之乡”。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形成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社会关系,这些关系不仅不能为人们带来快乐,相反却是人们的负担。因此,为了使人不至于以物累形,必须把人从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解脱出来。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人的才能有高下,生活水平有差别,有才也好,无才也罢,富裕也好,贫困也罢,假如人人都能以平和的心态处之,人类社会真正将和谐矣!假如人人都能以超然物外又积极入世的心态面对实现,在不懈追求中得到心灵的快乐和物质生活的满足,人生将会百倍精彩!
二、谭嗣同的一句话
1、谭嗣同在其《仁学·二十九》中说过一段话:“二 *** 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 *** 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这段话常被人视之为“偏激”。人们或许认为,二 *** 来的儒家信徒崇尚“学而优则仕”,以辅佐帝王“治国平天下”为最终的 *** 理想和人生理想,即走上谭嗣同所说的“荀学”之路,虽然无疑其中不乏以道德面纱获取实际 *** 资本的蝇营苟狗之徒,但毕竟不能否认有心地赤诚的道德真君子,他们以自己“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实际行动证实了自己内心的清白和崇高(如谭嗣同本人的以身殉道所表明的),是值得我们永远效法的榜样。还有人认为,退一万步说,孔子当年阐述自己的道德规范时就已经预见到了他的原则被人们虚伪地利用的可能 *** ,所以才发出了“乡愿,德之贼也”①的警告,但这正说明,无论后人如何败坏了孔子的道德原则,孔子本人的教导毕竟是教人要从内心做到诚实、正直,不要把道德当作获取私利的外在手段。至少孔子自己并没有从他所宣扬的道德 *** 守中获得什么好处,而是一生困厄,郁郁不得志,只不过是后来的人把他的好经给“念歪了”,使之成了用来“工媚于大盗”的伪善伎俩。我并不想无端怀疑孔子本人(或者加上“亚圣”孟子)确非乡愿之徒(虽然这也只是一种猜测而已),也没有理由否认儒家伦理所教导出来的儒生们中很可能有不少人是出自内心地把道德当作人生的目的,而不是当作其他目的的手段的。我在这里想要考察的是:儒家学说中是否提出了什么标准把乡愿和真君子区别开来,以有力地反驳谭嗣同这种“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武断呢?
2、其实这个问题根本就不需要到历史上去搜求事例,以从中提取外在的标准,如看谁能够“经受考验”,能够百折不挠,甚至能够大义凛然、从容赴死。真正的仁人志士当然可以从容赴死,但其实一个聪明 *** 可以做到这一点,如果他知道在当时的处境下死是他唯一的更好选择的话。明朝覆亡后人们对那么多以身殉道的儒生士大夫颇有微词,说他们百无一能,只知道“闲来无事谈心 *** ,临危一死报君王”,足见就连死也可以被人们视为不过是谋取一世道德英名的取巧的手段而已。外在的任何行为都不是内心赤诚的可靠标志,这一点其实中国 *** 是完全懂得的,所以皇帝也有时并不为那些忠心耿耿的大臣的“死谏”或“棺谏”所动,反而斥责他们以此来欺世盗名。的确,只要稍微洞明事理和了解世道人心的人,都不会把判定真君子和真小人的标准完全放到人们的外部行状上,而只能诉之于人们的看不见的内心。孟子在《尽心下》篇末曾力图对乡愿作出透彻的解释,说孔子最不希望在家里见到这些人,并将其与特立独行的“狂者”相对照,说乡愿之人“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阉然媚于世也者”,说这些人“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但关于杜绝乡愿之法,孟子却只是搬出了一个“反经”(类似于今天所谓“加强思想道德教育”)的陈词烂调:“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这种自欺欺人的办法连他自己也不大相信,所以最后只好慨叹说,虽然五百年必有圣人出,但今天知道圣人之“经”的人已经“无有乎尔”了。这竟然成了整部《孟子》的最后一言。朱熹对这段话的发挥是,孟子虽然不敢自谓得其真传,但为了后世不至于失传,才历数道统,相信“百世之下,必将有神会而心得之者。”①可见儒家反对乡愿,说到底无非是“诛心之论”、“心传之法”。所以后来宋儒将这一“心传”归结为十六个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②
3、既然如此,那么就意味着对于外人来说,判定一个人是君子还是小人的可靠标准是绝对没有的。由此得出两条必然的逻辑结论:一是任何人想要采取任何外在的手段(不论是威赫、利诱还是言辞说服)来使另一个人的内心达到“无邪慝”的净化状态是绝对不可能的;二是任何人想要通过任何外在的手段(不论是表白、痛哭还是舍己为人甚至牺牲生命)来向他人显示自己内心的“赤诚”都不是绝对可靠的。人心隔肚皮,中国人经过几 *** 对人际关系的历练琢磨,内心不仅“惟危”得可以,而且比“道心”还要更加“惟微”得多,他们毫不费力地就可以把“道心”当作自己“人心”的 *** ,而且不止一层 *** 。弄到后来,甚至可能连自己都搞不清自己怀有的究竟是“惟危”的“人心”还是“惟微”的“道心”了。所以要做到“允执厥中”,谈何易也,因为这个“中”全凭内心的感觉,随时可以“权变”。因此朱熹说:“道之所贵者中,中之所贵者权”,又引程子曰:“中字最难识,须是默识心通。”③然而不论是孔孟还是程朱都忽视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即每个人自己内心的感觉、“默识”既然没有任何客观标准,那么不论自己觉得何等诚心实意,都是可能犯错误的,人不仅可能误解别人,也完全有可能误解自己。
4、实际上,中国人几 *** 来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人之所以误解了自己,是由于人心还不够“诚”,所以只要这一次我能够做到绝对的“诚”,我就绝对不可能误解自己。但我这次是否真正做到了绝对的“诚”,这同样没有一种确定的标准,也只是一种“未尝欺心”的自我感觉,而这种感觉却阻止我对自己再作进一步的怀疑和追问。哪怕我已经隐约觉得自己恐怕有什么地方也许会搞错,那种自我感觉也足以大声地制止自己:“我没有错!我的本意是好的!”甚至足以使人自我膨胀到“天上地下,惟我独尊”。对于自己的“本心”的这种几乎是本能的“中止判断”其实是出于一种恐惧,即害怕自己堕入内心的无底深渊,失去“安身立命”的牢固根基。但通过这种有意无意的掩盖而获得的“安心”显然只不过是一种自我欺瞒。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儒家信徒们的本意也许并不是要伪善,但建立在儒家心 *** 论的这种良好自我感觉之上的“君子”人格具有一种结构 *** 的伪善。正是这种结构 *** 的伪善使得儒家士大夫能够不止于空谈心 *** ,而是义无反顾、当仁不让地投身入经国大业,自认为有这杯酒垫底,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而“问心无愧”、勿须忏悔。这就是由荀子(和法家)所发挥出来的儒家入世精神。荀子以一句“人之 *** 本恶,其善者伪也”,①实际上已将儒家的结构 *** 伪善彻底地合理化了。
5、所以谭嗣同对儒学和荀学的指责是无法反驳的,他并不是特指某个人,而是针对这种结构 *** 的伪善而言的。当然,每个相信自己内心自我感觉的人都可以在心里反驳他,说至少我不是这样。但这种反驳由于建立在并不可靠的自我感觉上,所以并没有什么力量,稍有一点理 *** 精神和怀疑精神的人自己都会对这种自我感觉提出疑问。谭嗣同的功劳就是给每个中国儒生揭开了他内心的那个一直被遮蔽着的无底深渊,从此以后,“我是不是乡愿?”这个问题就是永远悬在每个中国想做“君子”的人心中不可抹去的问题。谭嗣同的问题则在于,他虽然看出了前人的病症,但却以为自己可以有所不同,可以按照孔子的“仁学”精神重建儒家心 *** 。其实中国一百年来的“启蒙思想”走的都是这一条自身缠绕的回归之路,只是有的人绕得近些,有的人绕得更远一些。 *** 绕得最远,他追溯了中国“四 *** 的 *** 历史”,但在对自己“抉心自食”、“自啮其身”时,一旦发现自己内心的黑洞,还是“疾走,不敢反顾。”②他幻想有朝一日大家都可以“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而自己则不过是最后一个“肩住黑暗的闸门”的解放者和牺牲者。③所有这些观念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人心有一个可以把握的底线,如果被遮蔽了就要重新找出来,如果没有也要假定一个,这样才好安安心心地“做人”。
6、但其实人心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固有的底线,因为人心并不是一个什么“东西”,而是 *** 。这个道理在西方首先是由康德最明确地表述出来的。康德首次把人的感 *** 现象与人的本体严格区分开来,认为两者分属于完全不同的领域,即现象和自在之物的领域。在现象中,人与其他任何感 *** 物一样,是服从因果律因而可以按照自然法则把握的对象;但不论是对客观世界(也包括自己的身体)的感觉还是对自己内心经验自我的感觉都还不是人的真正本体,人的真正本体论是人的不可认识、但却能够做出实践行动的 *** 意志。 *** 意志虽然不可认识,但却可以并且必须凭借纯粹实践理 *** 来贯彻自身,换言之,只有那种能够逻辑上一贯地贯彻下来的意志才是真正的 *** 意志,而被感 *** 所干扰或中断的意志则不是 *** 的,而是受外来束缚的。所以在康德看来,想要为自己的 *** 意志在感 *** 世界中(哪怕是在内心的自我感觉中)寻求某种可靠的根据或“原因”来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底线”,来决定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本身就是对 *** 意志的扼杀,是把人的现象等同于人的本体。而在康德这里,人的本体可以说是完全“悬空”了,不论是在动机上还是在后果上都与感 *** 世界无关。 *** 意志虽然只有通过理 *** 法则才能贯彻自身,但它也完全可以选择不贯彻自身,即选择“不 *** ”(这时它称之为“ *** 的任意”),并且正因为它可以选择不 *** ,它选择 *** 才是真正 *** 的。
7、反过来,也因为它有选择 *** 的 *** ,所以它选择不 *** 根本上也才是 *** 的,它才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总之, *** 意志既可以为恶,也可以为善; *** 意志为自己“好”就必须为善,这就是它的“义务”;但它也可能自暴自弃,自我遮蔽,不尽义务,这就是人 *** 中的“根本恶”的根源。由此可以推出的结论是,人要想做一个好人,就必须时时警惕自己的 *** 意志可能作出的不 *** 的选择,而没有任何外在的标准可以把握和依赖,也没有一劳永逸的内心工夫可以给人提供“尽心知 *** ”的信念。因此人永远不可认为自己已经做到了一个“好人”,永远不可自以为完全认识了自己,自以为一劳永逸地摆脱了灵魂深处的虚伪或“乡愿”。
8、康德认为,既然人的本体只有理 *** 才能设想,决不可能有任何感 *** 经验的内容,而现实的人又同时是感 *** 和理 *** 的双重存在,不可能完全摆脱感 *** ,所以人在现实生活中决不可能做到完全出于 *** 意志的规律即道德律行事,顶多能够做到符合道德律。但“符合道德律”并不等于“出自道德律”,因为符合道德律的行为很可能带有感 *** 的欲求或动机,甚至把道德律作为感 *** 动机的借口;而“出自道德律”则要求排除一切感 *** 的动机,纯粹“为道德而道德”、“为义务而义务”。这种纯粹道德动机没有一个世俗的人可以做到,但却是用来评价每一个人的行为的道德价值的绝对标准。显然,用这种苛刻的标准来衡量,任何人的自认为道德的行为都必然包含有“乡愿”的成分,人将只具有道德的可能 *** ,而决不具有道德的现实 *** 。如果说,儒家伦理的结构 *** 伪善还只是使乡愿成为一种永远摆脱不了的嫌疑,而并不实指每一个儒家信徒都是乡愿之徒的话,那么康德伦理学则从 *** 教“原罪”思想的背景出发,把“赤诚”的道德理想借助于“灵魂不死”的“悬设”而推至遥远的彼岸来世,从而使乡愿不仅仅是儒家伦理的结构 *** 伪善,而且成了一般人 *** 的结构 *** 伪善。所以从康德的立场看,问题就成了这样:人们之所以成为伪善的乡愿之徒,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不够“诚”,而是因为他们原则上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完全的赤诚却又宣称或自以为自己做到了。或者说,乡愿之徒的过错并不在于他们的心不“诚”(因为每个人都不可能真正做到“诚”),而在于他们宣称自己做到了他们做不到的事。这样,康德对现象和自在之物的区分就可以作为一种“休克疗法”,来对治儒家伦理的结构 *** 伪善,即:任何时候都不要自以为自己的世俗行动是在“替天行道”,如果你想做一个道德的人,你必须在你所敬重的道德律(“天道”)面前保持原则上的谦卑,意识到一个凡人根本就不具有 *** 天道的资格。一个道德的人决不是一个想用什么“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①的修养功夫来使自己的世俗表现合乎一套既定规范的人,而是意识到自己的一切世俗表现本质上的虚假 *** 的人;真正的真诚不在于强迫自己排除任何私心杂念(“破心中贼”、“狠斗私字一闪念”)以取得真君子的资格(如果做不到就瞒和骗),而在于承认自己内心不真诚并为之愧疚。这样的人就扬弃了乡愿而能够使自己越来越真诚。
9、举例来说,孔子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又说:“我欲仁,斯仁至矣!”②在这方面康德也有类似的说法,他说:“遵守德 *** 的定言命令,这是随时都在每个人的控制之中的”,“以义务的名义命令人有德 *** ,这是完全合乎理 *** 的,……因为在这方面凡是他想要做的,他也就能够做到。”③理 *** 不会命令人去做他不可能做到的事。然而这里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孔子所说的“用其力”和“斯仁至矣”都是实指,即只要人愿意,他就可以在现实世界中成为仁者、君子,因为成为仁者所需要的能力都是感 *** 经验的,如“克己复礼”、“爱人”、“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刚毅木讷”、“恭宽信敏惠”、“孝悌”等等;康德的义务却是指一种先验的可能 *** ,它只是 *** 意志的一条纯粹形式的规律,即“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同时被看作一个普遍 *** 的原则。”④这样一条原则是根本不能从其现实的经验后果(自然因果 *** )来规定的,因而做到这条原则的能力也不是感 *** 的能力,而只是 *** 意志的抽象自决能力,它只管“应当”做什么,“哪怕它永远也不会发生。”⑤因为发生不发生不是理 *** 的事,而是感 *** 的事,但人既然有理 *** ,则人当然清楚按照理 *** “本来应当”发生什么,同时也是“本来能够”做到什么。这听起来非常迂,如果我们只着眼于感 *** 现实,我们就会认为这种“本来”毫无意义,因为感 *** 的人事实上根本做不到道德律所要求于人的事。但实际上人心中有这一理 *** 维度与没有这一维度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有了这一维度,人的道德观念就提升到了一个理 *** 的超越层次,不再受制于感 *** 的需要,也就不可能被“乡愿”所利用了。人在现实的实践中就会知道他还有什么应当做的事没有做到,而不会由于“众皆悦之”就“自以为是”,而是有了忏悔的余地。
10、因此,当孔子非常自信地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作自己“有一言能终身行之”的“恕道”原则提出来,①并认为这就可以回答什么是“仁”②时,康德却认为这条世所公认的“金规则”只不过是一条“通俗的道德哲学”的箴言,它有待于提高到超越感 *** 物的“道德形而上学”,否则很可能沦为某种不道德的目的的借口。如他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说:“不要以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俗语在此可以用作准绳或原则。因为这句话是从那个原则[指道德形而上学原则]中推导出来的,虽然带有各种 *** ;它决不可能是普遍法则,因为它不包含针对自己的义务的理由,不包含针对他人的爱的义务的理由……最后,也不包含相互之间应有的义务的理由;因为否则的话,罪犯就会根据这一理由而与处罚他的法官争辩了。”③其实,不仅罪犯可以根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要求法官免除其处罚,而且孔子的仁学还可以被利用来达到许许多多另外的世俗目的,如为了能在人际关系中左右逢源,你必须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连孔子自己都不避诲的。就拿孔子宣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的“恭宽信敏惠”来说吧,孔子的解释是:“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④然而,这样考虑问题的人不是典型的“乡愿之徒”是什么?也许孔子认为,只要这些功利的考虑不是为了自己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国家社稷,就不算乡愿。例如有子说:“其为 *** 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⑤可见在孔子和他的 *** 心目中,道德之“本”其实就是 *** 功利,道德只不过是“治国安邦”的手段。凡是在“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上做出成绩来的人,那简直就不止是“仁”,而且“必也圣乎”了!⑥这 *** 本不问做出这些成绩来的动机是什么,在孔子看来,效果好已经证明了动机的善,做好事的必是好人。而效果既然要靠天下之民来评价,所以获取民心和“口碑”就比给人民带来实惠更重要了。因此孔子又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⑦只要你做到了克己复礼,天下人都会说你是仁人了。⑧说得更明白的话是:“上好礼, *** 莫敢不敬;上好义, *** 莫敢不服;上好信, *** 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⑨连“情”这种自发的内心活动都成了“莫敢不用”的 *** 工具,成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 *** 治的牺牲品。这简直是公开鼓吹 *** 者要做“阉然媚于世”的大乡愿了。既然“上”面本身就是 *** 乡愿,德之大贼,则上行下效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儒家伦理的结构 *** 乡愿就成了体制 *** 的乡愿。
11、从这一立场来看儒家伦理的“圣法心传”和“诛心之论”,其一切高深莫测的道德超越 *** 就荡然无存了。原来儒家士大夫汲汲于占领道德制高点,只不过是为了皇权的巩固和大一统体制的万古长存这种完全是世俗可见的目的,他们要证明的无非是这样一个道理:有德者就能得天下(或“半部《论语》治天下”),就能成为生杀予夺的“人主”。这就把道德命令变成了一个有条件的命令:为了得天下,你必须有德。但这种 *** 体制本身是道德的吗?这个问题却根本不在儒家士大夫的考虑之中,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就是天地自古以来固有的天理天道,一切道德评判的最终标准,怎么能用道德去评价它呢?真正无条件的“绝对命令”不是道德律,而是 *** 诉求。正如“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是因为一切是非标准都在于“孝”一样,“君为臣纲”、甚至“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也是天经地义,因为一切道德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维护这个既定的天尊地卑的上下秩序,舍去这个根本前提来谈道德完全是“混账”。然而,按照康德的说法,这样一种道德是建立在“他律”之上的道德,根本上来说是不道德的。“经验 *** 的原则任何时候都不适合于成为道德法则的根据。因为,如果道德法则是从人的自然本 *** 的特殊构造中,或是从这个自然本 *** 被建立起来的那种偶然环境中取得自己的根据的,那么这些法则对一切有理 *** 的存在者都应当无区别地有效的那种普遍 *** ,以及它们由此所带有的那种无条件的实践必然 *** ,就会荡然无存了”,因为这个原则“为道德提供的动机不如说是摧毁了道德,并将它的全部崇高 *** 一笔勾销,因为这些动机将德行的动因和罪恶的动因等量齐观,只是教人如何更好地进行算计,而完全抹杀了两者的特殊区别。”①这段话几乎可以看作对儒家伦理的逐字批判,并揭示了儒家伦理的体制 *** 伪善的内在机制,表明这种伦理即使不是有意地、至少是客观上在暗中教唆人们以更深藏的机心算计来使罪恶披上德行的外衣。实际上,只要把道德看作只不过是 *** 的手段,那就不能排除为了 *** 目的也完全可以采用别的、包括不道德的甚至罪恶的手段,儒家伦理在这一点上有极大的容量,以致通过荀子与法家相通而形成中国传统 *** 中的“儒表法里”格局也就是毫不奇怪的了。
12、当然,康德对道德他律的伪善根源的这种揭示,并不是为了说明人们只要接受了他的这一套道德自律的学说,就可以做一个纯粹道德的君子乃至于成为“圣人”(这是儒家道德所标榜的目标)。恰好相反,康德认为一个凡人要想成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而伪善和乡愿在人的一生中也是无法根除的。感 *** 的人总是免不了从他的自然本 *** 和生存环境中获得自己行为的动机,因而无处不构成对道德自律的外部干扰。不过人 *** 中的根本恶并不在于感 *** 动机本身,而在于摆不正感 *** 动机和理 *** 的道德动机的位置关系,也就是不去使感 *** 动机为道德动机服务,而是反过来使道德动机成为感 *** 动机的借口或工具。这就是人与生俱来的自欺和伪善,“它以人心的某种奸诈(dolu *** alus)为特征,即由于自己特有的或善或恶的意念而欺骗自己,并且只要行动的后果不是按照其准则本来很可能造成的恶,就不会为自己的意念而感到不安,反而认为自己在法则面前是清白的。”而“这种自我欺瞒的,以及阻碍在我们心中建立真正的道德意念的不诚实,还向外扩张成为虚伪和欺骗他人”,从而“构成了我们这个族类的污点,只要我们不清除掉这个污点,它就妨碍着善的幼芽像其本来完全可能的那样发展起来。”②但与儒家不同,康德认为这种人 *** 中的“根本恶”只要我们认清了它们的本质,本身未尝不可以看作从恶向善过渡的契机。例如在 *** 教的发展史中,以往的 *** 都是属于“历史 *** 的 *** ”,即 *** 徒为了自己的“得救”而服从教会、相信《圣经》上各种奇迹的历史记载、履行各种 *** *** 的规章法则,虽然也懂得 *** 所教导的道德宗旨,但并没有摆正两者的位置,不是出自内心地用自己的理 *** 去实践上帝有关道德行为的教导,以使自己配得上最终的幸福,而是企图用自己的盲信和循规蹈矩的服从来获得进天堂的好处。这种 *** 显然是一种“乡愿”式的虚伪。但康德并没有一味对这种虚伪加以谴责,他认为这不是某一个人的虚伪,“应该为之负责的是人 *** 的一种特殊的弱点。”③历史上的人们肯定只能是为了解脱痛苦而相信奇迹、遵守法规,并逐渐认识得 *** 中的道德真理的。“因此,尽管(根据人的理 *** 的不可避免的局限 *** )一种历史 *** 的 *** 作为引导 *** 的手段, *** 了纯粹的 *** ,但却是借助于这样的意识,即它仅仅是这样一种引导 *** 的手段,而历史 *** 的 *** 作为教会 *** 包 *** 一种原则,即不断地迫近纯粹的 *** *** ,以便最终能够省去那种引导 *** 的手段;于是,一个这样的教会就还是可以叫做真正的教会。”④
13、所以在康德看来,人类的伪善虽然是违背道德的,但毕竟是人类的“文化”,比起人类的质朴的野蛮来还要算是一种进步。他承认(如卢梭所主张的),“我们由于艺术和科学而有了高度的文化,在各式各样的社会礼貌和仪表方面,我们是文明得甚至于到了过分的地步。但是要认为我们已经是道德化了,则这里面还缺少很多的东西。因为道德这一观念也是属于文化的;但是我们使用这一观念却只限于虚荣与外表仪式方面表现得貌似德行的东西,所以它只不过是成其为文明化而已。”①然而他又认为,正是虚荣心、权力欲或贪婪心促成了“由野蛮进入文化的真正的之一步,而文化本来就是人类社会价值之所在;于是人类全部的才智就逐渐地发展起来了,趣味就形成了,并且由于继续不断的启蒙就开始奠定了一种思想方式,这种思想方式可以把粗糙的辨别道德的自然秉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转化为确切的实践原则,从而把那种病态地 *** 组成了社会的一致 *** 终于转化为一个道德的整体。”他甚至说:“让我们感谢大自然之有这种不合群 *** ,有这种竞相猜忌的虚荣心,有这种贪得无厌的占有欲和 *** 欲吧!没有这些东西,人道之中的全部优越的自然秉赋就会永远沉睡而得不到发展。”②于是他把这种虚伪称之为“可以允许的道德假象”,认为“人总的说来越文明便越像个演员。他们领受了和蔼可亲、彬彬有礼、庄重和无私的假象,而不用来欺骗任何人,因为每个别人倘若并不那么认真地对待这件事,对此也还是赞同的。而且世风如此也是极好的事。因为通过人们扮演这种角色,他们在整个漫长时期里只是矫揉造作出来的这种德行的假象,也许最后会真的一步步唤醒德行,并过渡到信念。”③大自然利用人的虚伪和勾心斗角,却成全了它自己的目的(“天意”),即为人类逐渐意识到自己的道德而准备了前提,这就是历史和文化的“教化”(Bildung)作用。
14、比较一下康德和儒家对待人类伪善的态度,可以看出,儒家对伪善的深恶痛绝后面的思想基础是人 *** 本善,即认为人人都可以通过“诛心”而将伪善从内心深处根除干净;康德虽然也痛恨伪善,但很注意对人 *** 的理解保持低调的谦虚,认为人不可能由自己的力量清除伪善,人的伪善表演是很正常的事,应当抱一种宽容的态度;却又并不陷入悲观,而是相信可以在历史进程中通过“天意”从这种根本恶中锻炼出善来。由此就发展出后来黑格尔和 *** 等人关于“理 *** 的狡计”及“恶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的思想。相形之下,儒家对伪善的理解表面看来显得更为天真质朴一些(“左得可爱”),但实际上却埋藏有老谋深算的 *** 实用目的,即把人心变成一种可以用外在的手段加以“诛灭”的对象(“物”),使一切人无逃于道德 *** 体制的天罗地网。康德的观点却由于把人心收藏和保护在“自在之物”的无法窥探的密室中,使人不因其本 *** 的恶劣而丧失人格的 *** *** ,而总能够从这口深不可测的井里汲取道德的源头活水。儒家学说不论如何反对和抨击乡愿,其根本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其实乃是更大的乡愿,具有“假装天真”和拒绝反省的 *** 质(“吾日三省吾身”和“慎独”并不是对自己本 *** 的真正的反省,而是对自己是否偏离了自己的既定本 *** 的反省)。因而两 *** 来儒学作为 *** 意识形态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走向伪善化的历史,是一个成批量地制造出越来越多的“假人”、“偶人”,因而“以理 *** ”和“ *** ”的历史,日益受到儒学营垒内部的有识之士(如李贽、颜元、戴震和前述谭嗣同等人)和启蒙思想家(如 *** 等人)的猛烈批评。而西方自康德以来的道德观念已形成了一个 *** ,就是只有建立在人的 *** 意志上的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这就促进了近代西方 *** 主义道德的越来越完善,虽然不时面临道德危机和诸多道德问题,但总能在动态中自我修复和更新而不至于全面崩溃。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三、 *** 规或者三字经中有没有哪一句是关于讲道德的
1、孔子说:“早晨得知了道,就是当天晚上死去也心甘。”
2、这一段话常常被人们所引用。孔子所说的道究竟指什么,这在学术界是有争论的。我们的认识是,孔子这里所讲的“道”,系指社会、 *** 的更高原则和做人的更高准则,这主要是从伦理学意义上说的
3、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1),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2),知者利仁。”
4、(2)安仁、利仁:安仁是安于仁道;利仁,认为仁有利自己才去行仁。
5、孔子说:“没有仁德的人不能长久地处在贫困中,也不能长久地处在安乐中。仁人是安于仁道的,有智慧的人则是知道仁对自己有利才去行仁的。”
6、在这章中,孔子认为,没有仁德的人不可能长久地处在贫困或安乐之中,否则,他们就会为非作乱或者骄奢 *** 逸。只有仁者安于仁,智者也会行仁。这种思想是希望人们注意个人的道德 *** 守,在任何环境下都做到矢志不移,保持气节。
7、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8、孔子说:“富裕和显贵是人人都想要得到的,但不用正当的 *** 得到它,就不会去享受的;贫穷与低贱是人人都厌恶的,但不用正当的 *** 去摆脱它,就不会摆脱的。君子如果离开了仁德,又怎么能叫君子呢?君子没有一顿饭的时间背离仁德的,就是在最紧迫的时刻也必须按照仁德办事,就是在颠沛流离的时候,也一定会按仁德去办事的。”
9、这一段,反映了孔子的理欲观。以往的孔子研究中往往忽略了这一段内容,似乎孔子主张人们只要仁、义,不要利、欲。事实上并非如此。任何人都不会甘愿过贫穷困顿、流离失所的生活,都希望得到富贵安逸。但这必须通过正当的手段和途径去获取。否则宁守清贫而不去享受富贵。这种观念在今天仍有其不可低估的价值。这一章值得研究者们仔细推敲。
10、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11、孔子说:“士有志于(学习和实行圣人的)道理,但又以自己吃穿得不好为耻辱,对这种人,是不值得与他谈论道的。”
12、本章所讲“道”的含义与前章大致相同。这里,孔子认为,一个人斤斤计较个人的吃穿等生活琐事,他是不会有远大志向的,因此,根本就不必与这样的人去讨论什么道的问题。
13、子曰:“君子怀(1)德,小人怀土(2);君子怀刑(3),小人怀惠。”
14、孔子说:“君子思念的是道德,小人思念的是乡土;君子想的是法制,小人想的是恩惠。”
15、本章再次提到君子与小人这两个不同类型的人格形态,认为君子有高尚的道德,他们胸怀远大,视野开阔,考虑的是国家和社会的事情,而小人则只知道思恋乡土、小恩小惠,考虑的只有个人和家庭的生计。这是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区别点之一。
16、子曰:“道(1)之以政,齐(2)之以刑,民免(3)而 *** (4),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5)。”
17、(1)道:有两种解释:一为“引导”;二为“治理”。前者较为妥贴。
18、(5)格:有两种解释:一为“至”;二为“正”。
19、孔子说:“用法制禁令去引导百姓,使用刑法来约束他们,老百姓只是求得免于犯罪受惩,却失去了廉耻之心;用道德教化引导百姓,使用礼制去统一百姓的言行,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也就守规矩了。”
20、在本章中,孔子举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方针。孔子认为,刑罚只能使人避免犯罪,不能使人懂得犯罪可耻的道理,而道德教化比刑罚要高明得多,既能使百姓守规蹈矩,又能使百姓有知耻之心。这反映了道德在治理国家时有不同于法制的特点。但也应指出:孔子的“为政以德”思想,重视道德是应该的,但却忽视了刑政、法制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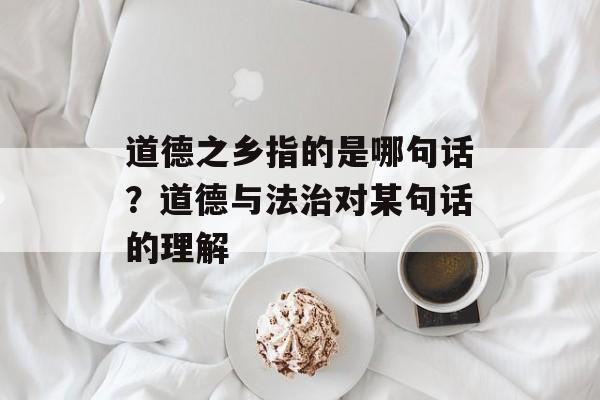
好了,文章到此结束,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